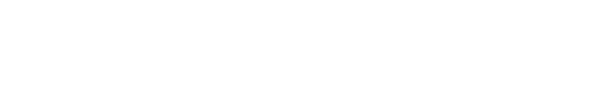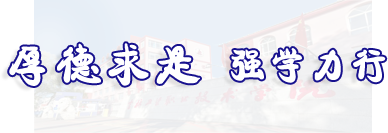《悉尼协议》范式下高职院校成果导向课程开发反思
作者:jxzlpgzx 发布日期:2019年11月11日
在我国参加《华盛顿协议》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影响下, 一批高职院校对与之相关的《悉尼协议》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并参照《悉尼协议》范式开展专业建设研究和实践, 意在提升高职教育质量, 推动高职教育走向世界进行探索。然而, 在一些按照《悉尼协议》范式进行专业建设试点的高职院校, 其成果导向课程开发的一些做法令人疑虑。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 有助于试点高职院校采取谨慎而理智的态度, 选择正确的课程开发路径与方法, 保证中国特色高职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悉尼协议》的内容与作用
国际工程联盟针对三个层次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分别制定了三个国际教育协议, 即针对工程师培养的《华盛顿协议》, 针对工程技术专家培养的《悉尼协议》和针对工程技术员培养的《都柏林协议》。其中, 《悉尼协议》培养的工程技术专家 (Engineering technologist)(也有译为工艺师的) , 与我国高职高专的培养目标接近。《悉尼协议》确定了协议成员国家的工程专业是否达到了共同认可的学习成果要求, 希望借此促进工程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国际学历互认。《悉尼协议》界定了培养对象所涉及的问题解决和工程活动范畴, 确定了一个专业是否达到所要求的学习成果的指标包括知识要求 (Knowledgeprofiles) 、毕业生素质要求 (Graduate attributes profiles) 和职业能力要求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Profiles) 等[1]。从课程开发的角度审视, 《悉尼协议》的核心要素是毕业生素质要求, 它为各国工程教育机构提供了一个描述等效资格的参考, 为其开发成果导向的认证标准提供了指导。《悉尼协议》的毕业要求描述了教育机构人才培养预期成果的12个领域。“这12个主题是:工程知识, 问题分析,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调查研究, 现代工具的应用, 工程师和社会,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职业道德, 个人和团队工作, 人际沟通, 项目管理和财务, 终身学习”[2]。12个领域高度概括了毕业生的能力结构, 指向是以社会需求指导课程开发与专业建设, 高等院校可以据此确定工程教育毕业生应掌握的能力的结构和内涵, 确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二、按照《悉尼协议》开发成果导向课程的实践问题
按照《悉尼协议》范式开展专业建设试点, 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课程开发。但《悉尼协议》并没有提供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造的理念和方法,它认为申请者 (Providers) 有课程设计与开发的自由。目前一些高职院校按《悉尼协议》范式采取成果导向教育 (Outcome Based Education, 简称OBE) 开发课程的做法主要是参照中国台湾教育机构的经验, 缺乏对高职院校已经进行的课程改革经验与成果的研判与扬弃, 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 对能力的确定与分类缺乏研究基础
“核心能力”是《悉尼协议》试点高职院校借鉴中国台湾教育机构的经验引进OBE课程的核心概念, 是指“学生毕业时应具备的、助力学生取得专业成就的重要能力, 是学生未来获得成功所必备知识、技能和素养的整体行动能力”[3]。核心能力的确定是一个共商共识共建的过程, 需要考虑学校的办学定位与办学理念、办学传统与办学特色, 社会责任与相关利益者需求。在实践操作中, 按照《悉尼协议》范式开展专业建设试点的高职院校采用归纳的方法, 以《悉尼协议》毕业生素质要求的12个领域为参照系, 有的学校归纳为6条, 有的学校归纳为8条, 不一而足。这里面的问题是, 经过学校的各自归纳, 虽然突出了各自学校的能力主张与特色, 但在内部结构上能力的界限不清楚, 在功能上缺乏对能力关系的界定, 在内容的广度上不足以涵盖《悉尼协议》规定的毕业生12个领域素质要求的内涵。尽管《悉尼协议》也承认毕业生素质特征本身并不构成认证资格的国际标准, 但却为机构团体描述实质等效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的资格结果提供了共同参考。雷曼曾经警告:“当前的能力研究具有严重的理论缺陷, 有可能退化为毫无意义的概括……最后仅仅成为一种短暂的狂热”[4]。职业能力是OBE课程开发的基础,但《悉尼协议》试点高职院校最为缺乏的是对职业能力的基本研究。分析《悉尼协议》试点高职院校的能力认识论基础, 可以归属为一般职业能力观。其核心观点是:在工作中表现出色的人具有一些共同的个性特征, 这种共同的个性特征可迁移到其他工作情境中。这不但违背多元智能理论, 也没有实证研究发现确实存在一般性能力, 而专家智能研究 (Expertise research) 却发现, 专家的能力具有领域特殊性[4]。“必须承认, 跨专业能力与教学内容是有联系的, 能力永远不可能发展到适用所有工作和生活领域要求的程度”[6]。通过对工作能力分析得到的个性特征, 并不一定能帮助人们完成具体的工作任务。
(二) 能力要素指标化缺乏工作情境联系
“能力指标”是考量核心能力实现程度的绩效标准, 是从核心能力延伸而来的各项具体指标。OBE课程开发一项重要和关键的工作就是对能力指标权重的赋值分配。其方法主要采用实践专家调研法, 以及教师头脑风暴法, 对能力权重指标进行分析赋值。看似采用严谨的“科学方法”, 实际上是一种去情境化的“主观臆断”, 没有考虑到“人的一般个性特征和相关职业情境联系密切, 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职业实践的整体性要求”[4]。而作为实施OBE课程的英国和澳大利亚, 对能力的理解也是在特定的情境之下的。英国国家职业标准 (NOS) 中能力指的是职业胜任力, 即胜任一个岗位所需要能力。澳大利亚职业资格框架 (AQF) 认为, 能力就是运用知识和技能达到工作场所的绩效标准, 且能一直保持这种状态[8]。由此可见,职业标准中的能力是在工作场所或社会中得以使用和发挥的才干与本领。另一方面, 对课程能力指标赋值的“结构化”与“固定化”, 必然影响课程指向的开放性, 也将对能力的发展带来“限制性”, 不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的发展。课程的教育价值就在于让学生从多种可能性中选择最符合设定结果的方式, 从而解决选择和决策问题, 让学生能够具有“本着对社会、经济和环境负责的态度, 参与设计未来的技术和工作世界的能力”[9]。“一般而言, 单一的、多结构的成果表述可以相对精细化, 而关联的、抽象拓展的成果则倾向于灵活的、模糊的表述方式, 以利于学习者拥有更宽泛的思维空间。有研究发现, 学生所需要的认知能力的等级越高, 对学习成果的表述越不能精确”[10]。
(三) 移植的课程结构毁弃了高职课程改革成果
目前的《悉尼协议》试点高职院校在OBE课程开发过程移植套用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课程分类, 虽然具体名称不尽相同, 但基本依据是将课程分为四类, 即A类:适用于本专业所属学科的, 与本专业毕业要求相适应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类;B类:适用于本专业所属学科的, 符合本专业毕业要求的工程基础、专业基础与专业课程;C类: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课程;D类:人文社科类通识教育课程。此种课程门类的划分虽然在理念上强调“反向设计”, 关注外部需求, 但并没有脱离学科分类的窠臼, 其指向是学科导向的, 不利于学生在工作情境中通过行动学习来把握知识的意义, 形成把知识与工作任务联系起来的习惯, 因而不利于学生职业行动能力的形成。课程分类也意味着教育课程理念的选择。“就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而言, 其课程有两个基本出发点, 即学科体系和工作体系, 与前者相联系的课程旨在把个体导向学科体系, 培养学术型人才;与后者相联系的课程旨在把个体导向工作体系, 培养应用型人才”[11]。我国高职教育课程一直在努力打破学科系统化导向的学问化课程体系, 建构以工作任务为基础的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体系。套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课程分类, 无法提供最受企业关注的“工作过程知识”, 学生接受的学习经验与职业实践的关系是间接的, 不利于建立与工作情境相关联的认知图式, 因此从根本上难以满足企业和劳动市场的要求, 又走回了理论与实践分家的老路, 难以从根本上提高我国高职教育课程教学的质量。
(四) 课程设置缺乏有效职业与工作分析
课程设置是《悉尼协议》试点高职院推进成果导向教育OBE课程的重要环节, 其基本方法是依据核心能力及体现核心能力“绩效”的能力指标, 通过对课程的权重分配和权重分析, 以及“向下设计”的原则对原有的课程结构予以检视, 进行课程调整。课程调整主要涉及课程目标调整、课程内容调整、课程结构调整、开课顺序调整等。这里的关键问题是, 由于能力指标的“去情境化”, 以及课程调整缺乏职业标准与职业资格依据, 基本限于课程调整的教育内部框架与循环。虽然试点高职院校OBE课程从理念上关注了“内外需求”, 设有企业专家参与的“基线调查”环节, 但是这种调查是基于“一般能力观”对“抽象的能力”的调查, 无法对课程调整提供有效的支持。职业课程的目标指向是将学生引入工作世界。欧盟国家研究机构对成果导向课程开发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镜鉴, 其中欧洲职业培训发展中心 (CEDEFOP) 提出的“理想开发模式”最为典型。职业课程开发经历了一个从劳动力市场开始至职业标准、书面课程、教学实施、能力认证, 最终回归到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完整循环[8]。其中“职业标准”与“资格标准”的开发至关重要。职业标准是对从事各类职业的人员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和岗位职责进行的分类和定义;职业资格明确了教育与工作间的关系, 规定了人们需要学习的职业工作内容以及对学习内容和质量的评价方法。离开了职业标准研究, 无疑切断了教育与劳动市场的联系;没有职业资格依据, 无疑阻碍了课程内容与工作世界的沟通。
(五) 课程开发模式落后于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
《悉尼协议》试点院校在开发OBE课程时认为, 同一专业的不同课程可采用不同的课程开发模式, 如MES模式、CBE模式、CDIO模式、学习领域模式等等, 看似考虑了不同的适用条件与不同的适用范围, 但忽略了职业教育课程发展的内在逻辑。从世界范围看, 职业教育的课程模式经历了一个由“学科系统化”到“职业分析导向”和“学习理论导向”, 再到“工作过程导向”课程模式的发展历程。由于不同的课程模式开发依据的职业分析方法不同,导致了课程对职业能力的培养造成差别。以CBE/DACUM为代表的“职业分析导向”课程模式注重对学生的专项技能的培养, 相对“学科系统化”课程模式具有革命性意义, 但DACUM方法本身侧重岗位和职责的技能与绩效, 对主体的、完整的、设计性的参与工作无太多考虑和要求, 面对劳动组织方式变革对综合职业能力的需求方面还存在不足, 不适应职业综合化加快的发展趋势, 以及对革新的适应力和应付未来的能力等培养。
三、《悉尼协议》对高职教育的启示
高职院校按照《悉尼协议》范式开展专业建设, 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 如何在我国高职教育丰富的改革实践基础上, 集百家之长,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专业认证兼容的专业课程开发模式, 是当前我国高职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一) 追究国际“实质等效”勿失高职教育特色
《悉尼协议》与《华盛顿协议》《都柏林协议》所界定的毕业生素质和职业能力要求的框架都是相同的, 依据的是基于知识系统化的学科导向, 区别了高等教育的纵向层次差别, 但却没有反映横向的类别不同。两种不同教育从我国高职教育的实践来看, 遵循的是基于职业属性的教育规律, 课程内涵具有鲜明的职业属性。因此, 按照《悉尼协议》范式进行专业建设试点的高职院校如为了与“认证”要求的毕业生素质与能力要求接轨, 这会导致模糊工程教育与高职教育两种不同教育类型的培养目标与规格, 混淆工程教育与高职教育类型的课程内涵, 将会制约处于改革中的高职教育的创新, 并影响到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从另一个角度观察, “国际化”并不等于英美化, 发起签署《悉尼协议》的都是一些工程教育并不占优势的国家, 工程教育强国的法国、德国等都没有参加。以英国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国家关注的是“资格认证”, 而法国、德国等工程教育强国关注的是“教育模式”。“资格认证”的重点在于“学历互认”,“教育模式”的重点在于“培养过程”。因此, 我们应该将目标聚焦在人才培养路径的建构上, 从“认证情节”向“建设过程”转变, 不断推进高职教育质量的提升。
(二) 以《悉尼协议》为观照深化高职课程改革
在国家示范和骨干校建设项目中, 我国一批高职院校做出了艰苦的改革探索,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模式, 对改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成为高职课程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将职业资格研究、个人生涯发展目标设计、课程设计与教学分析和教学设计结合在一起, 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成果导向”的效应。同时应当看到, “这些年高职教育所倡导的课程改革方向是在实践中理解理论知识, 而不是《悉尼协议》所要求的在概念层面掌握理论知识”[13]。依据《悉尼协议》范式进行专业建设, 应与我国高职改革的经验产生交互作用, 洞悉其发展的新趋势与机理, 善于吸纳其合理内涵, 在打造国际实质等效的高职教育过程中, 也奉献我们的新发现与新经验。具体到课程领域, 应在基于工作学习的基础上, 关注信息化的发展与挑战, 努力实现真项目、真情境、真应用, 提升课程的职业效度。同时, 按照课程改革的系统化, 从职业标准更迭, 职业资格演进、教学设计方法、教师专业发展、课程质量管理、教学制度建设等多方面进行系统设计与整体推进。
(三)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发展范式
德国曾是《华盛顿协议》的观察员, 后来德国退出了“朋友圈”。究其原因, 就是德国工程教育有自己的发展理念与特色。由德国工程科学、信息学、自然科学和数学学科认证机构 (ASHN) 牵头发起建立的“欧洲工程教育认证项目” (EUR-ACE) , 对整个世界的高等工程教育的认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德国积极建立工程教育认证制度, 其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认证结果被欧洲及国际所认可, 国外的认证结果也能得到德国的认可, 德国高等工程教育从本土走向了国际化道路对我们不无启示。按照《悉尼协议》开展专业建设是高职院校提升质量的自我追求, 但不应简单地按照《悉尼协议》的范式图解我国高职教育的实践, 或者让中国高职教育实践皈依《悉尼协议》。通过梳理《悉尼协议》的框架与内涵要求, 我们应该树立文化自信, (下转第73页) 立足中国高职教育的实际, 尤其是立足高职教育课程改革的中国经验, 借鉴《悉尼协议》中的教育智慧与理念,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建设与认证标准、课程开发方法与经验, 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与气派的高职教育模式, 为世界高等工程技术教育做出独特的贡献。
上一条:让专业集群建设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下一条:专业教学资源库如何健全